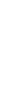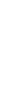男变女之肉欲纪事_御书屋 - 第144章就当女人
空气里还氤氲着刚才那番关于“天生一对”的对话所留下的、心照不宣的笑意,以及一种被共同秘密烘烤出的、粘稠而诡异的温暖。我枕在苏晴单薄却异常稳当的肩膀上,脸颊贴着她丝质睡裙微凉的布料,鼻息间全是她身上那种混合了清晨洁净与复杂过往的独特气息。窗外的阳光彻底明亮起来,穿透薄纱窗帘,在餐厅的木质地板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,连带着空气里悬浮的细小尘埃都镀上了一层金色,活泼地舞动着。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涂抹上了一层不真实的、慵懒而甜腻的糖霜,连那过于炽烈的光线都因此显得柔和暧昧,令人昏昏欲睡。
就在我几乎要溺死在这麻痹般的舒适与奇异安宁感中时,苏晴忽然又开了口。她的声音依旧平稳清淡,仿佛只是随手从脑海中捞起一个无关痛痒的念头,闲聊般提起。然而,那平铺直叙的语调下,抛出的问题却像一道毫无征兆的、裹挟着冰碴的闪电,猝然劈开了我小心翼翼维持的、摇摇欲坠的迷梦。
“晚晚。” 她叫我的名字,指尖依旧无意识地、带着一种近乎宠溺的韵律,缠绕把玩着我散落在她肩头的一缕乌黑发丝,发丝柔软顺滑,在她指间绕成小小的圈。“问你个问题。”
“嗯?” 我懒洋洋地应着,意识像是漂浮在温水里,眼皮沉甸甸地往下坠,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也带着浓重的睡意和餍足后的绵软。
“如果……” 她顿了顿,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目光从把玩的发丝上移开,转而落在我近在咫尺的侧脸上,那目光平静,却带着审视的穿透力,“我是说如果……有机会,让你变回林涛……变回男人……你愿意吗?”
变回林涛。
变回男人。
这八个字,组合在一起,像一把被冻得坚硬无比、尖端闪烁着寒光的冰锥,猝不及防地、狠狠地刺穿了我这些日子以来,用“晚晚”这个崭新身份、用这具年轻柔韧的女性躯体、用这几天接连不断的混乱、放纵、算计与扭曲温情,辛辛苦苦、摇摇欲坠构筑起来的心灵堡垒。
愿意吗?
一个几乎要冲破喉咙的、源自本能的呐喊,几乎立刻就要脱口而出——“当然愿意!”
哪个曾经作为男性存在过的人,会心甘情愿、永远被困在一具截然不同的、属于异性的身体里?更何况,这具身体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,已经承载了太多……屈辱(主动或被动)、精心的算计、以及那些混杂着痛楚与极致欢愉的、不堪回首的性体验。
但,就在那声呐喊即将冲破唇齿的瞬间,却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、厚实的墙壁,猛地哽住了,卡在喉咙深处,灼烧着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变回林涛……那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变回那个在职场中不上不下、努力挣扎却始终看不到清晰前途的平庸男人;变回那个在婚姻围城里一败涂地、眼睁睁看着曾经深爱(或许?)的妻子投入他人怀抱、自己却连愤怒都显得苍白无力的失败者;变回那个最终在绝望与不甘中选择“消失”、将烂摊子留给一个新生灵魂的……懦夫。
意味着失去“晚晚”这张看似柔弱无害、实则蕴含着无限可能与便利的、“年轻美丽女性”的“王牌”。再也无法利用这份天然的性别优势和新鲜感,去接近那些曾经需要仰望或忌惮的人(安先生、王明宇),去实施那些模糊的报复计划,甚至……去“享受”某些原本绝无可能触碰的、背德的刺激。
意味着离开眼下这个虽然混乱不堪、危机四伏,却莫名让我感到一种诡异“自由”和前所未有“存在感”的欲望与秘密漩涡。在这里,道德枷锁松动,身份标签模糊,一切行为似乎都可以用“混乱”来解释,从而获得某种扭曲的豁免。
更意味着……再也无法体验到……
我的思绪,不受控制地、如同脱缰的野马,猛地挣脱了此刻慵懒的氛围,疾速倒流。
它流回昨天下午那辆飞驰的、弥漫着情欲气息的车厢里——安先生那具年轻、强悍、充满原始爆发力的躯体,是如何将我(这具身体)彻底压制、贯穿,带来几乎要将灵魂都撞碎、却又令人战栗沉迷的极致快感。那种纯粹依靠体能和雄性本能的、野蛮的征服,是“林涛”绝对无法给予,也绝无可能体会的。
它流回更早之前,那些与王明宇共度的、充满权力碾压与利益交换的夜晚——那双总是冷静自持、仿佛能掌控一切的手,是如何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和精准的技巧,在我身上烙下属于他的印记。那种混合着明确屈辱、却又在生理上无法完全抗拒、甚至偶尔会催生出扭曲快感的“被征服”体验,同样是“林涛”视角下,绝对无法理解、更无法“享受”的复杂感受。
甚至……我的思绪流连在了此刻,就在刚才,苏晴的指尖缠绕我发丝时,那带着奇异安抚与亲昵意味的触碰;流连在她昨夜耐心揉按我胀痛胸口时,那混合着观察、抚慰与微妙占有欲的复杂温度;流连在她用平静语调说出“天生一对”时,那双美丽眼睛里罕见的、近乎温柔的笃定。
这些感受,这些互动,这些建立在“晚晚”这个女性身份之上的、复杂难言的关系与情绪……是“林涛”那个身份,从未、也永不可能体验和拥有的。
一种强烈的、混杂着对未知未来的恐惧,和对眼前这混乱现状难以割舍的留恋,如同两只无形的大手,猛地攥紧了我的心脏,带来一阵窒息般的闷痛。
苏晴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我身体的瞬间僵硬,以及随之而来的、长达数秒的死寂般的沉默。她没有催促,没有流露出任何不耐或好奇,只是静静地等待着,仿佛早已预料到我会陷入这样的挣扎。连她手上把玩我发丝的动作,也悄然停了下来,指尖悬在半空。
时间,在餐厅温暖明亮的晨光里,被拉得无比漫长。远处隐约传来城市的喧嚣,更衬得此刻的寂静令人心悸。
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,久到窗外的光影都似乎偏移了一点点,我才听到自己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般的声音,从喉咙深处艰难地挤出来,带着明显的不确定和一种自我剖析般的、深深的迷茫: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”
这个回答,软弱,含糊,毫无底气。它暴露了我内心的巨大矛盾与动摇。
苏晴低低地“唔”了一声,那声音很轻,听不出具体的情绪,更像是一种表示“听到了”的回应,或者是……一种“果然如此”的了然。
然后,她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在为我此刻显而易见的犹豫和迷茫,做一个最残酷也最直白的注解。她的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静,甚至带上了一丝飘渺,然而吐出的字句,却字字诛心,像最锋利的刀刃,剥开所有矫饰:
“是不是……被操爽了……离不开男人的大肉棒了?”
“轰——!!!”
这句话,比刚才“变回男人”的问题,更具毁灭性的杀伤力,也更赤裸,更粗俗,更羞辱到了极致。
像一盆刚刚从滚油锅里舀起、却又混杂着千年玄冰碎块的、肮脏不堪的液体,毫无预兆地、兜头浇下!
“你——!” 我猛地从她肩头弹开,像是被烙铁烫到,脊背瞬间挺得笔直,几乎是弹跳般转回头,瞪向近在咫尺的她。脸上的血色在刹那间褪得干干净净,惨白如纸,随即又因为极致的羞愤和某种被戳穿的恐慌,猛地涨红,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!嘴唇不受控制地剧烈哆嗦着,牙齿甚至磕碰在一起,发出细微的“咯咯”声,却连一个完整的音节都吐不出来。
是愤怒吗?因为被她用如此不堪的词汇形容?
是羞耻吗?因为内心最隐秘、连自己都不敢正视的角落,被她如此精准、如此残忍地撕开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?
还是……恐慌?恐慌于她竟然真的看穿了我,看穿了我对这具身体所体验到的、那些混杂着痛楚的极致快感的留恋,看穿了我对那种被强悍雄性力量彻底占有、填满时的扭曲沉迷,甚至看穿了我对“女性”身份所能带来的、某些特殊“便利”与“体验”的……隐秘依赖?
她怎么可以……怎么可以用这么粗鄙、这么直接、这么……一针见血的话语,来定义我此刻所有的挣扎和犹豫?
我想反驳,想尖叫着否认,想用最恶毒的语言回击她,维护自己最后一点可怜的、早已碎成齑粉的尊严。
然而,就在我羞愤交加、无地自容,恨不得立刻挖个地洞钻进去或者当场消失的时候——
身体深处,某个最幽暗、最不受理性控制的角落,却有一个微弱到几乎听不见、却又无比清晰的声音,在剧烈地战栗着、挣扎着,最终,化为一声几不可闻的、充满自我唾弃却又无法否认的叹息:
或许……她说得对。
至少……有一部分是对的。
就在我被这灭顶的羞耻、愤怒和自我怀疑彻底淹没,意识模糊,几乎无法思考,只余下本能想要逃离这令人窒息境地的冲动时——
一个低沉、平稳、带着惯常威压感与不容置疑气场的男性嗓音,毫无预兆地、仿佛从虚空里凝结出来一般,从客厅连接餐厅的拱形门廊阴影处,清晰地响了起来:
“看来,我来的不是时候?”
这个声音……
我的血液,仿佛在听到第一个音节的瞬间,就彻底冻结了。一股寒气从脚底猛地窜起,顺着脊椎一路爬升到头顶,带来一阵剧烈的、生理性的冷战。全身的肌肉,连同指尖,都在刹那间变得僵硬、冰冷、麻木。
我极其缓慢地、像是生锈的机械般,一点一点地,转过头,视线越过苏晴的肩膀,带着巨大的、近乎绝望的迟滞感,投向声音的来源。
王明宇。
他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那里。穿着一身剪裁无比合体、线条流畅冷硬的深灰色定制西装,衬得他肩宽腰窄,身姿挺拔如松。他的双手随意地插在西裤口袋里,姿态看似闲适,却自带一股无形的、掌控全局的气场。晨光从侧面的大窗斜射进来,恰好照亮他半边轮廓分明的脸,挺直的鼻梁,薄而线条清晰的嘴唇,还有那双……深不见底、平静无波的眼睛。
他的目光,正以一种不疾不徐、近乎巡视领地般的节奏,平静地扫过铺着洁白桌布、摆放着简单早餐却无人动用的餐桌,扫过我和苏晴紧挨着、几乎依偎在一起的亲密坐姿,最后,精准地、稳稳地,落在了我的脸上。
他的眼神,一如既往,像两口结了冰的古井,表面平静,底下却仿佛涌动着能吞噬一切的暗流。他脸上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,只有一丝极淡的、近乎玩味的弧度,若有若无地挂在嘴角。
但我知道,他一定……听到了。
听到了我们之前那些关于“屁股撅高”、“发情母猫”的、不堪入耳的互相调侃。
听到了苏晴那个石破天惊的、关于“是否愿意变回男人”的致命提问。
更听到了……苏晴最后那句,足以将我所有羞耻心击得粉碎的、赤裸裸的判词——“是不是被操爽了离不开男人的大肉棒了”。
他全都听到了。
这个清晰无比的认知,像一只无形而冰冷的手,猛地攫住了我的心脏,狠狠捏紧。眼前瞬间阵阵发黑,视野边缘炸开一片片细碎的金星。羞耻感,前所未有的、排山倒海般的羞耻感,如同最深最冷的海底涌起的灭顶海啸,瞬间将我吞没、窒息。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指尖冰冷麻木得失去了知觉,全身的力气都在这一刻被抽干,骨架仿佛都要散掉,只想立刻缩成一团,化作尘埃,或者干脆立刻死去,以逃避这令人崩溃的境地。
我甚至不敢,连余光都不敢,去瞥一眼身旁苏晴此刻是什么表情。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、崩塌,只剩下王明宇那道平静却令人肝胆俱裂的视线,和我自己无处遁形的、狼狈不堪的灵魂。
王明宇迈开了脚步。
他的步伐不疾不徐,皮鞋质地优良的鞋底踩在光洁的木质地板上,发出清晰、稳定、富有节奏感的“嗒、嗒”声。那声音在死一般寂静的餐厅里,被无限放大,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紧绷到极致的神经上,带来一阵阵尖锐的刺痛和无法抑制的恐惧颤栗。
他没有看苏晴一眼,仿佛她只是这场景里一个无关紧要的背景板。他径直朝着我坐的这一侧走了过来。
我死死地低着头,几乎要把脖颈折断,视线牢牢地锁在自己绞在一起、因为用力而指节泛白、微微颤抖的手指上。那些精心修剪过、涂着透明护甲油的指甲,此刻深深掐进了掌心的嫩肉里,带来细微的刺痛,却完全无法分散注意力。我恨不得能把自己的头彻底埋进胸口,或者直接钻进面前这张坚实的实木餐桌底下。
他在我旁边的椅子前,站定。
阴影,伴随着他身上那股熟悉的、冷冽又强势的、混合着高级古龙水和某种无形威压的气息,沉沉地笼罩下来,将我完全覆盖。
“小林。”
他开口,叫的却是……“小林”。
不是“晚晚”。
是“小林”。那个他曾经用来称呼还是“林涛”时的我(作为他的下属或需要“关照”的对象)、带着清晰的上位者对下位者、金主对依附者的、既熟悉又充满了距离感与掌控意味的称呼。
这个称呼,在此刻,在此情此景下,被他用这种平静无波的语调叫出来,简直比任何直接的辱骂、斥责或暴怒,都更让我感到无地自容,羞愤欲死。它像一根最精准的刺,狠狠地扎进了我试图用“晚晚”这个新身份包裹起来的所有伪装,无情地提醒着我:无论我变成了什么模样,无论我经历了怎样光怪陆离的转变,在他王明宇的眼里,我似乎永远都是那个需要他“提携”、仰仗他“恩惠”、被他牢牢掌控在股掌之中的“小林”。我的挣扎,我的变化,我的混乱,在他面前,似乎都只是……徒劳的可笑。
我浑身无法控制地剧烈一颤,像是被无形的电流狠狠击中。头垂得更低,前额几乎要撞上冰冷光滑的桌面,呼吸屏住,连睫毛都在剧烈颤抖。
王明宇却似乎很满意我这副反应。他拉开我旁边的椅子,昂贵的西装面料与实木椅子摩擦,发出细微而清晰的声响。然后,他坐了下来。
距离很近。
近到他的手臂,几乎要贴上我裸露在睡裙袖子外、同样冰凉的手臂。他身上那股强大的、不容忽视的存在感和压迫感,如同实质的墙壁,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。
然后,我听到了他低沉的声音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、近乎戏谑的、猫捉老鼠般的笑意,贴着我滚烫的耳廓,响了起来:
“怎么不回答你‘老婆’的问题?”
他故意停顿了一下,仿佛在欣赏我因为他这句话而变得更加僵硬、几乎要碎裂的身体,和那骤然加重的、紊乱不堪的呼吸。
“嗯??”
他又叫了一遍,尾音微微上扬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追问和极致的羞辱。
我的脸颊滚烫得如同被架在火上炙烤,耳朵里充斥着血液奔流的巨大轰鸣,几乎要震破耳膜。羞耻、难堪、恐惧、绝望……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感到无比厌恶的、在他这种绝对的、居高临下的掌控姿态下,身体本能升腾起的、熟悉的战栗和近乎卑贱的服从欲……所有这些情绪如同沸腾的岩浆,在我体内疯狂冲撞,几乎要将我撕裂。
我不敢抬头,不敢发出任何声音,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,细弱游丝,仿佛稍微用力,就会引爆什么不可挽回的东西。
王明宇似乎几不可闻地轻轻叹了口气,但那叹息声里,没有丝毫温度,只有一种掌控者面对不听话的猎物时,那种混合着不耐与笃定的从容。他伸出手。
不是来碰我低垂的、布满泪痕的脸颊。
也不是来碰我紧绷的、微微颤抖的肩膀。
而是……
直接地、毫无缓冲地、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、理所当然的掌控姿态,从我的身体侧面,覆了上来。
他宽大、温热、指节分明的手掌,稳稳地、完全地,包裹住了我因为极度紧张和羞愧而无法控制地微微起伏的、左边的绵软胸脯。
隔着我身上那件单薄的、居家穿的浅蓝色棉质睡裙——里面是真空,昨夜被安先生和苏晴先后“照顾”过,此刻依旧敏感饱胀——他掌心的热度毫无阻隔地熨帖上来,带着一种绝对占有的力度。
“啊……” 我惊喘一声,声音短促破碎,像是濒死小兽的呜咽。身体猛地向后一缩,本能地想要逃离这突如其来的、充满羞辱意味的侵犯。然而,他坐得极近,手臂和身体形成的半包围圈,如同最坚固的牢笼,轻而易举地将我试图逃离的动作镇压、困住,让我动弹不得,只能僵硬地承受。
他没有立刻进行揉捏或爱抚,只是那样贴着,掌心传来的滚烫热度和沉甸甸的存在感,却比任何粗暴的动作都更具压迫力和宣告意味。仿佛在无声地说:看,无论你变成什么样,无论你和谁有了什么秘密,你身体的这一部分,依然在我的掌控之下。
紧接着,他覆在我胸口的那只手的拇指,开始极其缓慢地、带着一种评估物品质地般的、冷静而狎昵的力度,揉搓顶端那粒早已因为之前一系列的情绪刺激和此刻的羞辱,而悄然硬挺、肿胀的小小凸起。
力道不轻不重,恰到好处地既能带来清晰的刺激,又不至于让我痛呼出声。但那动作里蕴含的绝对掌控和狎玩意味,却比纯粹的疼痛更让我感到灭顶的羞耻和……某种被彻底支配的、熟悉的战栗快感。
我浑身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,被他触碰的那一点,像被点燃了引信的炸药,灼烧感混合着奇异的酥麻,迅速向四肢百骸蔓延。身体在他手下变得越来越软,越来越烫,意识也开始模糊、涣散。
“王总……别……求您……” 我带着浓重的、几乎泣不成声的哭腔,声音细弱蚊蚋,破碎不堪。徒劳地想要挣扎,身体却背叛了意志,在他持续而富有技巧的刺激下,越来越软,几乎要化成一滩水,瘫软在椅子里,只能依靠他手臂的支撑才不至于滑落。
“别什么?” 王明宇的声音依旧平稳,甚至带着一丝饶有兴味的笑意,仿佛在欣赏一场有趣的表演。然而,他手上的动作却变本加厉,从缓慢的揉搓,变成了带着狎玩意味的、不轻不重的掐捏,指腹恶意地碾过最敏感的尖端,“刚才不是跟你‘老婆’聊得挺开心?聊被谁操得爽?聊撅着屁股迎合的样子?”
他的每一句话,都像蘸了盐水的皮鞭,精准地、毫不留情地抽打在我早已溃不成军、鲜血淋漓的自尊心上。将我试图掩藏的最后一点遮羞布,也彻底撕碎、践踏。
“我……我没有……不是那样的……” 我徒劳地、微弱地否认着,眼泪终于再也控制不住,如同断了线的珍珠,大颗大颗、无声地滚落下来,划过我滚烫的脸颊和脖颈,滴落在他昂贵挺括的、深灰色手工西装袖口上,留下深色的、耻辱的湿痕。
“没有?” 王明宇低低地笑了一声,那笑声里没有任何愉悦,只有冰冷的嘲弄和掌控一切的了然。他另一只手也抬了起来,这次,精准地捏住了我的下巴,用不容抗拒的力道,强迫我抬起那张布满泪痕、狼狈不堪、梨花带雨的脸,逼我看向他。
他的眼睛很近,很近。那双总是深不见底、仿佛能洞悉一切的寒潭般的眼眸,此刻清晰地映出我此刻的模样——满脸泪痕,眼神涣散羞耻,嘴唇被自己咬得红肿,头发凌乱,睡衣领口歪斜,胸口还被他的一只手牢牢掌控、揉弄着……一副彻底被摧毁、被征服、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姿态。
“,” 他看着我,捏着我下巴的拇指,缓缓地、带着狎昵的力度,摩挲着我湿漉漉的、微微红肿的下唇,语气近乎一种残忍的温柔,和下流的逼问,
“回答我。”
他的气息喷在我的唇上,带着他特有的冷冽味道。
“还想变回男人吗?”
他的目光,如同最沉重的枷锁。
他的手掌,如同最灼热的烙铁。
他的气息,如同最无法挣脱的网。
他的一切,都在此刻,构成了一个绝对封闭、无法逃离的审判场。
而我的身体,在他持续不断的、充满技巧与羞辱意味的揉弄刺激下,早已彻底背叛了所有残存的意志和理智,变得滚烫如火,湿润如潮,颤抖如风中落叶。
最后一丝试图维持尊严、试图抵抗的理智堤防,终于在这多重夹击下,轰然倒塌,彻底崩溃。
我看着他那双近在咫尺的、充满了绝对掌控欲和冰冷审视的眼睛,看着里面映出的、那个卑微可怜、完全臣服的自己。忽然,不知道从哪里,涌上来一股破罐破摔的、近乎疯狂的勇气(或者说,是彻底堕落的决心)。
我猛地吸了吸鼻子,不再试图挣脱他捏着我下巴的手,反而就着这个被迫仰头、完全暴露脆弱颈项的姿势,用那双泪眼朦胧、水光潋滟,却在此刻奇异地带上了一种彻底放弃挣扎后的、近乎妖异的媚意的眼睛,直直地看向他。
然后,我做了一个让王明宇眼神骤然微凝、深邃眸底掠过一丝清晰的诧异,也让旁边一直沉默如背景、仿佛置身事外的苏晴,几不可查地、轻轻挑了一下眉的动作。
我猛地、用尽全身残余的力气,推开了身下的椅子(王明宇配合地、适时地松开了些许捏着我下巴的力道)。椅子腿与地板摩擦,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下一秒,我转过身,在晨光刺眼的餐厅里,在王明宇深沉目光的注视下,直接跨坐到了他的腿上。
面对面。
双腿分开,跪坐在他结实的大腿上。米白色丝质睡裙的裙摆因为这个动作而向上堆迭,露出大半截光裸的、线条优美却微微颤抖的大腿肌肤。我伸出双臂,环住了他的脖颈,将满是泪痕、滚烫的脸颊,紧紧地贴在了他挺括冰冷、质感高级的西装前襟上。
像一个在暴风雨中终于找到唯一浮木的、恐惧无助的孩子,不顾一切地寻求庇护。
又像一个自知罪孽深重、只能献上自身所有作为祭品的、卑微而放荡的娼妓,主动将自己送入掌控者的手中。
我能清晰地感觉到,在我跨坐上去的瞬间,他整个身体骤然紧绷了一瞬,肌肉在昂贵的西装布料下贲张,散发出更加浓烈的、不容错辨的侵略性和雄性荷尔蒙的气息。随即,那紧绷又缓缓放松,变成一种更从容、更充满掌控意味的接纳。
我靠在他坚实宽阔的胸膛上,隔着衬衫和西装,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。我用带着浓重鼻音、未散哭腔,却又奇异地揉入了一种娇媚入骨、近乎撒娇般的甜腻的声音,贴着他胸口微凉的布料,呢喃般地说道:
“我……我孩子都为你生了……”
这句话,像是一个提醒,一个筹码,也是一种……对自我最终定位的、绝望而彻底的确认与投降——我是你的女人,为你孕育过子嗣、打上过最深烙印的女人。无论我内心有多少混乱、多少不甘、多少对过往身份的留恋,这具身体,这个名为“晚晚”的存在,从最根本的生物学和社会关系上,都已经与他(王明宇)紧密地、无法分割地捆绑在了一起。这是我的“原罪”,也是我此刻唯一能抓住的、证明自己“存在意义”的浮木。
王明宇的身体,在听到这句话后,似乎几不可查地放松了些许。他环在我腰后的手臂收紧,将我更紧、更牢固地固定在他腿上,让我们的身体贴合得密不透风。那只原本覆在我胸口揉捏的手,并没有停下,反而顺着我腰侧柔滑的曲线,灵活地、不容抗拒地,滑进了我睡裙宽大松散的下摆。
指尖带着常年养尊处优却依然存在的、细微的薄茧,划过我大腿内侧那片最为敏感娇嫩的肌肤,引起一阵阵无法抑制的、触电般的剧烈战栗。
然后,毫无阻碍地,长驱直入,探向腿心那片因为刚才持续的情绪刺激和羞辱,早已变得泥泞不堪、湿热滑腻的隐秘入口。
“唔……!” 我浑身剧烈地一颤,像是被最强烈的电流瞬间贯穿所有神经。双腿下意识地、本能地用力夹紧,试图阻挡这过于直接、过于侵犯的触碰。然而,这个夹紧的动作,却恰好将他探入的手指,更紧密地、严丝合缝地绞在了那片湿滑温热、不断收缩蠕动的核心地带。
“啊……” 我发出一声压抑到极致、却又充满情动沙哑的呻吟,身体在他怀里彻底软成一滩春水,所有的力气都被抽空,只能完全依靠他的支撑,随着他手指的节奏,无力地微微起伏、颤抖。
王明宇的手指并没有急着向更深处探索,只是就着被我双腿紧紧绞缠、吸附的姿势,在那片湿滑泥泞、门户大开的入口处,缓慢地、研磨般地、极具技巧性地搅动、按压。每一次刮擦,每一次按压敏感的内壁软肉,都带出更多羞人而清晰的“咕啾”水声,和一阵阵直冲天灵盖、让我灵魂都快要出窍的灭顶快感。
他的唇贴在了我滚烫的耳廓上,呼吸灼热滚烫,喷吐在我敏感的耳蜗和颈侧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清晰,带着不容置疑的、最终判决般的命令口吻,和一丝终于不再掩饰的、赤裸裸的、强大的占有欲:
“以后……”
他故意顿了顿,被我双腿绞住的手指,恶劣地、向湿热紧致的甬道深处,浅浅地探入了一小截,立刻感受到了内壁疯狂的、高频的收缩和吸吮,像无数张小嘴贪婪地咬住、挽留。
“只准当女人。”
这四个字,他说得又慢又重,像四颗被烧得通红、淬了最烈毒药的钉子,狠狠地、一锤一锤地,钉进了我的灵魂最深处。
剥夺。
彻底的剥夺。
剥夺了所有关于“变回林涛”、关于恢复男性身份的可能性与幻想。
将我,永远地、牢固地,钉死在了“晚晚”这个女性身份之上。
然后,是最后的宣判,也是最赤裸的契约:
“给我操。”
最后三个字,他说得更慢,更重,字字千钧,带着一种不容违逆的、野兽般的占有宣言。像最滚烫的烙铁,带着毁灭与重生般的痛楚,狠狠地烙印在我颤抖的灵魂和这具注定归属于他的身体上。
只准当女人。
给他操。
这是一个最终判决,也是一个终身契约。
它抹杀了我所有关于“过去”的留恋与不甘,也堵死了所有关于“不同未来”的模糊想象。
它将我,“晚晚”,永远地、彻底地,钉死在了他王明宇的掌控之下,钉死在了这具只为承受他(或许,还有其他被他允许或默许的?)欲望而存在的女性躯体里,钉死在了这场由他主导的、混乱而危险的游戏规则之中。
羞耻吗?
是的,铺天盖地,灭顶而至。如同最深最冷的深海,将我彻底淹没,窒息。
绝望吗?
或许。对那个名为“林涛”的、已经模糊的过去,和所有关于“正常”、“自由”的可能性的,彻底的、冰冷的绝望。
然而,在这灭顶的、几乎要将我灵魂都冻结的羞耻与绝望的冰冷深海最深处……
在那被他手指持续搅动出的、越来越汹涌澎湃、几乎要将我意识彻底冲垮的滚烫快感浪潮中……
在这被绝对力量压制、被彻底宣判归属的、无处可逃的境地里……
我竟然,可悲地、却又无比清晰地感觉到……
一种扭曲到极致的、近乎畸形的安心感,和归属感。
仿佛一颗在惊涛骇浪中飘摇无依、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种子,终于被一只强大而冷酷的手,强行按进了某片虽然贫瘠荒芜、危机四伏,却至少是“坚实”的土壤里。哪怕这片土壤充满毒质,哪怕未来可能暗无天日,但至少……有了一个“地方”。
一个确定的、无法更改的、属于“晚晚”的“地方”。
我闭上眼,滚烫的眼泪,如同决堤的河水,无声地、汹涌地滑落,浸湿了他胸前的西装布料。然而,我的手臂,却更紧、更依赖地环住了他的脖子,仿佛那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我的身体,诚实地、甚至带着一种卑微的迎合,随着他手指那充满掌控意味的节奏,微微地、无法自控地起伏、磨蹭。喉咙深处,溢出破碎的、断续的、如同最卑微臣服与承诺般的呜咽。
“嗯……” 我听见自己用几乎只有气声才能发出的、微弱的音量,回应道,像是对那最终判决的接受,像是对那终身契约的画押,更像是对自己这具身体和灵魂最终归宿的、绝望而认命的确认,
“……只给你操……”
餐厅里,阳光刺眼夺目,将一切照得无所遁形。
王明宇稳稳地抱着跨坐在他腿上、衣衫不整(睡裙凌乱)、泪痕交错却媚态横生、身体随着他手指动作微微颤动的我。他的面容依旧沉静,眼神深邃,仿佛刚才只是完成了一场理所当然的、微不足道的“驯服”与“确认”。
而这场“驯服”与“确认”,在这明亮得近乎残忍的晨光中,无声地、却无比深刻地,改变了某些东西的走向,也最终锚定了“我”——“晚晚”——在这片混乱泥沼中的……位置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
发送任意内容至邮箱po18de@gmail.com获取最新访问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