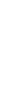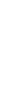男变女之肉欲纪事_御书屋 - 第149章搬新家了
我侧躺着,呼吸在黑暗中清晰可闻。身下是顶级埃及棉的床单,冰凉滑腻,贴着我的小腿肚。卧室里只开了一盏光线柔和的壁灯,在墙角投下暖黄色的、模糊的光晕,勉强勾勒出巨大房间的轮廓——昂贵的抽象画,冷灰色的墙面,线条极简的家具。空气里飘着我和苏晴各自沐浴后留下的、清淡又截然不同的香气。我的,是王明宇准备的、某个小众品牌的樱花混合白麝香,甜得有些刻意;苏晴的,则是她一贯喜欢的、更清冽的雪松与佛手柑,带着距离感。
“林晚。” 苏晴的声音在寂静里响起,不高,却像一颗石子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。
我的心跳漏了半拍,指尖无意识地蜷缩起来,抵着自己睡衣的袖口。那件睡衣是浅珊瑚粉的真丝吊带裙,细得几乎看不见的肩带,V领开得不低,但丝绸柔软服帖,能隐隐透出胸前起伏的曲线。长度刚好到膝盖上方,随着我侧躺的姿势,裙摆微微上缩,露出一截同样光裸的大腿。这是我作为“林晚”后,逐渐习惯(或者说被迫接受)的睡衣款式之一。王明宇似乎偏爱这种若隐若现的材质和裁剪,它们无声地强调着这具身体的女性特质——纤细的锁骨,柔软的胸脯,不盈一握的腰,以及笔直修长的腿。起初穿上的每一刻都让我如坐针毡,仿佛“林涛”的灵魂在被这轻薄的丝绸公开处刑。但现在,身体的记忆已经开始适应这种触感,甚至在微凉的夏夜里,会觉得比保守的棉质睡衣更舒适贴肤。
“嗯?” 我应了一声,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有些轻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我没有转头,视线落在对面墙上那幅我看不懂的抽象画上,仿佛那扭曲的色块里藏着什么答案。
身侧的床垫传来轻微的动静,是苏晴也侧过了身,面对着我。即使闭着眼,我也能感觉到她目光的落点。我们之间隔着大约一个人的距离,像一条无形的楚河汉界。
“没什么,” 苏晴的声音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斟酌词句,或者只是单纯地感受着此刻的气氛,“只是觉得……有点不真实。”
不真实。这个词精准地戳中了我们共同的心境。
白天,我们是“晚晚阿姨”和“妈妈”,穿梭在这座如同现代艺术馆般冷清又奢华的半山别墅里。别墅的空间大得惊人,三层楼,落地窗永远擦得锃亮,映出窗外连绵的绿意和远处城市模糊的天际线。昂贵的意大利家具线条冷硬,颜色以黑、白、灰为主,偶尔点缀着金属或玻璃的冷光,处处透着王明宇个人审美的简洁与疏离。幸好,妞妞彩色的蜡笔涂鸦,乐乐散落在客厅地毯上的乐高零件,还有健健学步时碰倒的玩具,像顽强的藤蔓,一点点侵蚀着这份冰冷的规整,带来了些许凌乱却真实的生活气息。
王明宇在物质上的确“大方”得无可挑剔。除了这栋别墅,他给“他的女人们”——我和苏晴——各自准备了一间卧室。都在二楼,门对着门,面积、格局、甚至内部装潢的风格都惊人地相似。米白色的墙壁,同款的原木色地板,巨大的步入式衣帽间,连接着带按摩浴缸和双人洗手台的浴室。衣柜里挂满了当季最新款的衣裙,从休闲到正式,从保守到性感,尺码精准地贴合我们各自的身材。梳妆台上摆满了我认不全牌子、但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护肤品和化妆品。一切都完美得像五星级酒店的套房,或者说,像两个精心布置的、对称的展示柜,或者观察室。我有时会阴暗地猜想,王明宇在准备这些时,是否也带着某种玩味的、如同摆弄棋盘般的期待,想看看被他放在对局的“棋子”们,私下会如何相处,如何选择。
白天的日常被孩子们填满。妞妞七岁,刚上小学,梳着两个整齐的羊角辫,说话脆生生的,像只精力充沛的小麻雀。乐乐八岁,正是调皮的年纪,但对“晚晚阿姨”有种莫名的亲近,或许是因为我(林涛)残留的、对待儿子的本能方式?健健最小,刚学会跌跌撞撞地走路,咿咿呀呀,是这栋过于安静的房子里最鲜活的声音。
接送上下学,准备点心,检查作业,陪玩,处理孩子们之间的小摩擦……这些琐碎的事务,有保姆分担大部分,但我和苏晴还是默契地亲力亲为着与孩子们直接相关的部分。在这过程中,我和苏晴之间,形成了一种奇特而微妙的状态——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与挥之不去的生疏,如同水与油,看似共存,却界限分明。
默契,根植于那七年名义上的婚姻生活。即使作为“林涛”的我,在婚姻后期早已心力交瘁、同床异梦,但那些日复一日积累下来的、关于家庭运转的肌肉记忆却顽固地留存着。她知道乐乐吃鱼要挑干净刺,我知道妞妞睡前一定要听哪个特定的故事。当她自然地接过我递过去的、乐乐忘了签名的试卷时,当我顺手帮妞妞整理好她玩闹时扯松的蝴蝶结发绳时,那些流畅的、无需言语的配合,偶尔会带来一阵短暂的恍惚。仿佛时光倒流,还是“林涛”和“苏晴”,在那个不算宽敞但充满烟火气的家里,一起打理着他们共同的孩子和人生。那一刻,“林晚”这个崭新的、年轻的躯壳仿佛透明了,底下是“林涛”笨拙却熟悉的灵魂,在对苏晴做着曾经做过无数遍的小事。
但这种恍惚转瞬即逝,随即被更尖锐的现实刺破——那便是无处不在的“生疏”。
这生疏源于一切早已天翻地覆。我是“林晚”。镜子里的脸只有二十岁,肌肤光洁饱满,几乎看不见毛孔,五官是清纯中带着不自知的妩媚——眼尾微微上挑,嘴唇是自然的嫣红色,不笑时也像含着情。身高165公分,体重被严格控制在45公斤左右(王明宇似乎偏好这种纤细骨感),骨架小巧,脖颈修长,肩膀单薄,锁骨清晰。栗色的长卷发每天早晨需要花些时间打理,才能保持那种蓬松慵懒又精致的弧度。声音是清亮的少女音,说话时尾音会不自觉地微微上扬,带着天然的娇软。连走路的姿势,都在王明宇有意无意的“矫正”和这具身体本能的适应下,变得轻盈,甚至……带着点不自觉的摇曳。尤其是穿着裙子的时候,小腿的线条,脚踝的弧度,都成了我自己视线里陌生又熟悉的风景。
而苏晴,是那个我曾以“林涛”的身份爱过、依赖过,又因她的出轨和冷漠而恨过、痛苦过的前妻。现在,她是我这具新身体名义上的“姐妹”,是我们共同男人王明宇的另一个情人。我们曾在他面前赤裸相对,共享过他的身体,甚至在那混乱的情欲中,有过难以启齿的肢体接触。每一次,当我们的目光在不经意间于客厅、厨房、或是楼梯转角相撞,空气中便会瞬间弥漫开一种粘滞的、充满复杂电波的沉默。不是尴尬,而是一种混合了过往恩怨、现在共处一室的荒诞、以及那些共享过的、淫靡记忆的无声发酵。递东西时指尖短暂的触碰,并肩坐在沙发上看孩子玩耍时衣料摩擦的细微声响,甚至只是闻到她身上飘来的、那款我(林涛)曾经很熟悉的香水尾调……所有这些日常的细节,都成了触发那混乱记忆库的开关,让平静的日常水面下,暗流汹涌。
而夜晚,当孩子们都沉入梦乡,健健被保姆抱回婴儿房,偌大的二楼归于寂静时,那种“生疏”与“连结”并存的张力,便达到了顶点。
两扇相对的门,是敞开,虚掩,还是紧闭?
睡不睡一张床?
这成了我们住进这里后,每个王明宇不在的夜晚,无声上演的内心戏。
第一个他缺席的夜晚,我们并排坐在客厅那张宽大得过分的奶白色沙发上,中间隔着足以再塞进一个成人的距离。巨大的电视屏幕里播放着喧嚣的综艺节目,五彩的光影在我们脸上明明灭灭,却谁也看不进去。
“妞妞今天又问,”苏晴忽然开口,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寂静。她手里捧着一杯温水,眼睛盯着屏幕,侧脸的线条在落地灯柔和的光线下显得清晰而柔和。她今天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,里面是同色系的丝质吊带,下身是浅咖色的宽松休闲裤。长发松松地挽在脑后,几缕碎发垂在颈边,有种居家的随意,却依旧透着一种被良好滋养和精心维护过的精致感。三十三岁,生育过两个孩子的身体,在她自律的管理下,呈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丰腴与紧致,尤其是胸部和臀部的曲线,比我(林晚)更具成熟女性的圆润风韵。她的气质很特别,眼神大多数时候清澈甚至带着点纯真感,但偶尔沉静下来时,眼底会掠过一丝我(林涛)当年未曾完全读懂、如今才隐约触摸到的深沉,以及……那些放纵过往留下的、难以言喻的痕迹。
“为什么晚晚阿姨和妈妈,不住在一个房间。”她继续说道,声音平静,听不出太多情绪。
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攥了一下。孩子们的世界相对单纯,他们只是本能地觉得,妈妈和这个熟悉的、对他们很好的“晚晚阿姨”(他们或许对“爸爸林涛”还有模糊的印象,但被告知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,而晚晚阿姨是来帮忙照顾他们的“新阿姨”),理应是最亲密的伙伴,应该住在一起。
“你怎么说?”我问,声音因为干涩而有些发紧。我身上穿着同款的针织开衫,不过是浅灰蓝色的,里面是那条珊瑚粉的真丝睡裙。空调温度打得低,裸露的胳膊和小腿能感觉到微微的凉意,这让我不由自主地将自己蜷缩得更紧了些,怀里的羽毛抱枕被压得变形。
“我说,房间多,分开住舒服。”苏晴抿了一口水,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,“但她好像不太满意这个答案。”她放下杯子,陶瓷底座与玻璃茶几接触,发出清脆的轻响。
沉默再次像潮水般涌来,淹没了综艺节目里虚假的笑声。
“乐乐倒是没问,”我试图找点话,让这凝滞的空气松动一些,声音刻意放得轻快些,“男孩子可能不太在意这些细节。”
“他在意。”苏晴却立刻否定了我的猜测,她转过头,目光直直地看向我。壁灯的光映在她眼里,亮晶晶的,里面翻涌着太多复杂的、我一时无法完全解读的情绪。“他今天偷偷问我,晚晚阿姨是不是以后就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了,像……像以前爸爸那样。”
“像以前爸爸那样”。
这短短几个字,像一把小而钝的刀子,缓慢而精准地旋进了我(林涛)灵魂最深处的旧伤口。乐乐记忆里的“爸爸”,是那个三十七岁、身高只有一百六十五公分、在人群中不算起眼、或许也没能给他提供多么优渥生活、但曾努力想用肩膀撑起一个小家的普通男人。而现在,他每天面对的“晚晚阿姨”,是这副年轻、漂亮、声音娇柔、被王明宇圈养起来的女性身体。
“你怎么回答的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飘忽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
“我说,是的,晚晚阿姨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。”苏晴顿了顿,目光没有移开,反而更加专注地落在我脸上,那视线带着审视,探究,还有一丝……或许是连她自己都没完全理清的复杂情感。“乐乐听了,好像……松了口气。”她又补充道,语气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涩然。
空气再次陷入沉默,但这一次的沉默里,多了些沉重的东西。
“她还说,”苏晴的声音再次响起,比刚才更轻,却字字清晰,“希望晚晚阿姨晚上能陪她睡。她说新房子太大,她的房间也有点……空,她有点怕黑。”
这是一个契机。一个顺理成章、可以打破眼下僵局、满足孩子愿望的契机。
但也是一个陷阱。一个可能会让我们不得不直面彼此之间那团乱麻、将模糊的界限彻底揉碎的陷阱。
我抱着抱枕,指尖无意识地捻着上面细腻柔软的绒毛。身体里,属于“林晚”的这部分——这个二十岁、心思相对单纯、对孩子们有天然亲近感、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习惯了女性身份和思维方式的“我”——对于“和苏晴同床”这个念头,似乎并没有产生强烈的、本能的排斥。甚至,因为对妞妞和乐乐的疼爱,觉得陪孩子睡、或者至少和“妈妈”一起让孩子安心,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就像大学女生宿舍里,关系好的闺蜜偶尔也会挤在一张床上夜谈。
但身体里,那属于“林涛”的灵魂碎片,却在激烈地翻腾、挣扎。羞耻感如同冰冷的藤蔓缠绕上来——作为前夫,和出轨的前妻、现在共享同一个男人的情人同床共枕?抗拒感在尖叫——这意味着对“林涛”男性身份最后一点象征性坚持的放弃。然而,在这羞耻与抗拒的底层,却又可悲地翻涌着一丝对“曾经拥有”的、病态而苍白的怀念,以及对那七年婚姻生活中、无数个同床异梦却又真实存在的夜晚的、遥远而模糊的记忆。
“主卧的床很大。”苏晴忽然开口,语气听起来很随意,就像在评论窗外的天气,或者电视里某个明星的穿着。“王总准备的,大概是考虑过……偶尔的需要。”她的话尾音微微上扬,带着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、了然的讥诮。
王明宇确实可能存着某些恶趣味。他或许乐于看到,他放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“收藏品”,在私下里,会如何相处,如何磨合,如何在这由他设定的诡异关系网中,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这张巨大的床,或许本身就是他恶趣味的一部分。
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,然后在胸腔里擂鼓般急促起来。她这是在邀请吗?用这样一种近乎直白又留有转圜余地的方式?还是说,她仅仅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,一个我们都心知肚明、却谁也不愿轻易点破的可能性?
我抬起眼,看向她。她也正看着我,没有移开视线。在暖黄壁灯的光晕里,她的眼神不再有白天的闪躲或刻意的平静,而是直接地、带着某种复杂难言却清晰有力的东西,与我的目光在空中相接、碰撞。那眼神里,有我们共同走过的七年婚姻,平淡、争吵、背叛与和解;有对“林涛”这个存在(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前夫)的复杂情感光谱——爱过吗?或许。恨过吗?肯定有过。愧疚呢?也许藏在深处。有对“林晚”这个突然出现、占据了“林涛”位置、又年轻得刺眼的存在的困惑、不解、甚至一丝隐隐的嫉妒;有对“我们都是王明宇女人”这个尴尬身份的微妙认同与无奈;甚至……还有对那几次在情欲巅峰、理智崩坏时,三人纠缠中,身体与身体之间短暂而深刻的触碰、温度、乃至反应的……记忆。
空气仿佛被抽干了,每一寸都充满了无形的张力,绷紧,再绷紧。
要不要睡一张床?
睡,意味着什么?是对那段失败婚姻形式的一种可悲又无奈的模仿与延续?是对眼下这种畸形三人关系的被动妥协与默认?是为了安抚孩子不安心灵而做出的牺牲和让步?还是说,在我们彼此都经历了这么多背叛、伤害、共享男人甚至共享过彼此身体触感的混乱之后,在灵魂和肉体都被打上复杂印记之后,某种超越简单定义、更复杂、更混沌、更难以言喻的情感联结或依赖,正在这荒诞的土壤里,悄然滋生?
不睡,又意味着什么?是固执地划清界限,强调我们现在仅仅是“王明宇的情人A和情人B”,除了孩子和那个男人,再无其他瓜葛?是逃避面对我们之间这团理不清、剪不断的乱麻,维持表面平静下的暗流汹涌?还是对“林涛”那早已逝去的男性身份和社会角色,进行最后一场无谓的、无人观看的哀悼与挽留?
我的手指将抱枕的绒毛揪得更紧,指节微微泛白。身体深处,似乎传来一阵细微的、莫名的悸动,像是紧张,又像是……隐约的期待?
“孩子们……”我终于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,很轻,带着明显的不确定和一丝颤音,“可能会觉得更安心。妞妞怕黑的话……”
苏晴的眼神似乎闪烁了一下,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掠过湖面。她没有立刻回应,而是微微移开了目光,重新投向电视屏幕上变幻的光影,但肩膀的线条,似乎几不可察地放松了一点点。“嗯。”她应了一声,声音也低了下去,比刚才多了点别的意味,或许是释然,或许是别的什么。“而且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组织语言,或者是在鼓起勇气说出下一句,“这房子……太大,太空了。晚上……安静得有点……过分。”
她承认了。
尽管措辞委婉,但她确实承认了某种程度的不安,或者更确切地说,是寂寞。即使她曾经玩得那么“花”,有A先生那样长久而热烈的情人,即使她现在也和王明宇保持着这种复杂纠缠的关系,被物质和欲望层层包裹,但在这样一个由金主安排、关系诡异、如同精美鸟笼般的“家”里,在孩子们都睡去后,夜晚降临,无边无际的寂静如同潮水般漫上来时,那种深切的、浮萍般的无根感,那种身处繁华却内心荒芜的孤独……我们或许,在这一点上,是相通的。再多的物质,再混乱的关系,也填不满某些时刻,灵魂深处悄然裂开的缝隙。
这个认知,像一道微光,穿透了我们之间厚重的、充满过往尘埃的隔阂。
“那……”我深吸了一口气,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,抱着抱枕站了起来。珊瑚粉的真丝睡裙随着我的动作如水般滑落,贴在身上,勾勒出纤细的腰肢和臀腿的轮廓。赤脚踩在微凉的原木地板上,脚趾下意识地蜷了蜷。“我去我房间,拿我的枕头和被子。”
苏晴也站了起来,动作比我从容些。米白色的针织开衫敞开着,露出里面丝质吊带的细腻光泽和饱满的胸部曲线。“用主卧的吧。”她说,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平静,但眼神里似乎多了点什么。“王总准备的床品……确实更舒服些。”她说着,转身走向她那扇敞开的卧室门,“我拿点我的东西过来。”
没有明确的“来吧”或“好的”,没有热情的邀请或郑重的应允。但行动本身,已经做出了最清晰的选择。一种心照不宣的、带着试探和妥协的默契,在沉默中达成。
主卧无疑是整层楼最大、视野最好的房间。那张巨大的Kingsize床,奢华得近乎夸张,床垫柔软而富有支撑力,躺在上面仿佛被云朵包裹。我和苏晴各自从自己的“领地”里,拿了些贴身的物品——睡衣,护肤品,一两本睡前翻看的书,还有对于我来说,一只妞妞送我的、丑丑的手工编织小熊。我们默默地将这些东西,分别放在床的两侧——我习惯睡左边,她似乎自然地选择了右边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放置动作,本身就充满了象征意味:划界,宣示各自的习惯和隐私范围;同时,也是一种妥协,默许了共享这个最私密空间的事实。
洗漱的过程在各自浴室里完成,水声隔着墙壁隐约可闻。当我换上另一套更为保守的棉质长袖长裤睡衣(下意识的选择,仿佛需要一层更厚的盔甲)回到主卧时,苏晴已经半靠在床头了。她换上了一套浅灰色的真丝分体睡衣,上衣是短袖衬衫式样,裤子宽松,长发披散下来,遮住了小半边脸颊,正在低头看着手机屏幕,暖黄的阅读灯在她脸上投下柔和的光晕。
我们互道了一声很轻的“晚安”,然后关掉了大部分光源,只留下我那侧一盏光线最暗的夜灯。
我躺在属于我的这一侧,身体僵硬得像个木偶。身下是顶级面料带来的极致舒适触感,鼻尖却萦绕着陌生的、属于这个房间的淡香,以及……从另一边飘来的,苏晴身上那熟悉的、清冽的雪松与佛手柑气息,混合着刚沐浴过的、干净的水汽。
沉默在黑暗中无边无际地蔓延。但这一次,不再是客厅沙发那种令人窒息的、充满对抗和尴尬的沉默。而是一种……奇特的、共享着同一片黑暗与寂静的、微妙的张力。我们能听到彼此清浅的呼吸声,能感受到床垫因对方细微动作而产生的、几乎难以察觉的起伏。我们之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,却仿佛能感觉到对方身体散发出的、温热的磁场。
“林晚。”
她的声音再次响起,比刚才更轻,更像是一声叹息,或者是一个试探性的气泡,小心翼翼地浮出黑暗的水面。
我屏住了呼吸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
发送任意内容至邮箱po18de@gmail.com获取最新访问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