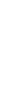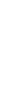男变女之肉欲纪事_御书屋 - 第234章都怀孕了
# 暮色中的两张试纸
傍晚的光线是金色的,却又带着一天将尽的疲惫,懒懒地透过卫生间那扇半磨砂的玻璃窗,斜斜地切进来,在弥漫着未散水汽的空气里,划出一道道朦胧的光柱。细密的水珠挂在光洁的瓷砖墙面上,缓慢地汇聚、滑落。空气里飘着我刚用过的、带着甜腻茉莉花香的沐浴乳气味,混合着热水蒸腾后的氤氲湿意,黏糊糊地附着在皮肤上。
我站在宽大的盥洗镜前,身上只松松垮垮地裹着一件米白色的纯棉浴袍,腰带在腰间随意打了个结,领口敞开着,露出大片被热水熏得微微泛红的胸口肌肤和清晰的锁骨。长发湿漉漉地披在肩头,发梢还在滴水,水珠顺着脖颈优美的曲线,滑入浴袍更深的领口,留下一道冰凉的湿痕。
镜子被水汽蒙上了一层薄雾,人影模糊。我抬起手,用掌心抹开一片清晰。
镜中的女人,脸颊被热水蒸出健康的红晕,眼睫上还沾着细小的水珠,眼神却不像刚沐浴后那般松弛。那里头有什么东西在微微闪动,像是平静湖面下悄然游过的鱼影——一丝难以精准捕捉的、混合着某种奇异柔光与……更深邃盘算的神采。我的目光,不由自主地、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探寻,缓缓下移,落在了自己依旧平坦如初、覆盖在柔软浴袍下的腰腹之间。
浴袍的棉质布料柔软地贴合着身体的曲线。我的手,像是被无形的线牵引着,从擦拭头发的动作中脱离,指尖带着沐浴后皮肤特有的微湿和敏感,小心翼翼地、隔着那层薄薄的棉布,轻轻落在了小腹的位置。
触感……似乎和以往有些微妙的不同。
不是形状的改变。那里依旧紧实平坦,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,年轻的肌肤紧贴着骨骼与薄薄的肌肉层。但指尖按下去,在柔软的脂肪和肌肉之下,仿佛能感觉到一种更深处的、难以言喻的……饱满?或者说,是一种沉睡般的、内里的凝滞感?像是有什么极细微的东西,在这具身体最深处悄然改变了密度,正在缓慢地、无声无息地酝酿、生长。
是错觉吗?还是……
田书记那张戴着金丝边眼镜、表情总是平静无波的脸,蓦地浮现在脑海。他那句低沉而清晰的承诺,不是回响在耳边,而是像一枚烧得通红的烙铁,直接烫在了心底最柔软的、也是最为贪婪的角落。每一次呼吸,每一次心跳,似乎都能感觉到那烙印的灼热温度。
指尖下的皮肤仿佛也因为这份联想而微微发烫。
如果真的有了……那里面跳动的,会是金币碰撞的清脆声响吗?
这个念头让我嘴角不受控制地向上弯起一个极小的、带着甜蜜与算计的弧度。镜中的女人也跟着笑了,那笑容映在逐渐清晰起来的镜面上,眼波流转间,那丝奇异的柔光似乎更盛了些,与眼底深处那片属于商人的精明冷光,交织成一种复杂而迷人的蛊惑力。
就在这时,指尖在洗手台冰凉的陶瓷边缘无意识地划过,却意外地碰到了一个柔软的、带着些微潮气的小小纸团。
我的动作顿住。
那不是纸巾。触感更粗糙,带着点硬质的芯。它被仓促地揉捏过,丢弃在洗手台与墙壁的夹角阴影里,并不起眼,若非指尖恰好划过,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我低下头,目光落在那个小纸团上。
心脏,毫无预兆地,轻轻抽动了一下。
一种莫名的、冰冷的预感,像细小的蛇,悄然滑过脊椎。
我伸出手,指尖有些发凉,捏起了那个潮湿的、带着洗手台水渍的纸团。很轻。我慢慢地、极其缓慢地,将它展开。
淋湿的纸面有些皱,有些地方的字迹和图案被水渍晕染开,变得模糊。但——
那两道并排的、刺目的、鲜艳到几乎要灼伤眼睛的红色线条。
在卫生间顶灯惨白而明亮的光线下。
清晰得如同命运落下的一记冰冷而决绝的判笔。
不是我的。
我的那份,那同样显示着两道红杠、被我反反复复确认过无数次的验孕试纸,此刻正被我小心翼翼地、用干燥的纸巾包好,藏在卧室梳妆台那个带锁的、最隐秘的夹层抽屉深处。像藏着一把通往未知却金光闪闪未来的、绝密的钥匙,也像藏着一个一旦曝光就可能引来腥风血雨的、甜蜜而危险的炸弹。
那么,这张……
血液仿佛在看见那两道红杠的瞬间,彻底冻结,不再流动。四肢百骸一片冰冷。但下一秒,更加喧嚣狂暴的热流,又猛地从心脏泵出,疯狂地冲上头顶!耳朵里嗡嗡作响,眼前甚至有一瞬间的发黑。
我捏着那张皱巴巴、湿漉漉、却带着惊心动魄证据的纸,指尖冰凉得像是浸在雪水里。
不是我的。
那只能是……
一个名字,带着那个总是沉默、隐忍、却又在关键时刻会露出一种让我心惊的平静眼神的身影,猛地撞进脑海。
我猛地转过身,浴袍的下摆因为急促的动作而扬起。赤足踩在冰凉微湿的瓷砖地面上,几步就跨到卫生间门边,一把拉开了磨砂玻璃门。
门外,卧室里光线已经暗了许多。夕阳最后的余晖从通往小露台的落地玻璃门斜射进来,给房间里的家具镀上了一层虚幻的、暖金色的边。空气里飘着淡淡的、属于这个“家”的、混合了皮革、实木和昂贵香薰的味道。
苏晴正斜倚在那扇玻璃门边。
她身上穿着一套浅灰色的、质地柔软的丝绸家居服,上衣是宽松的圆领长袖衫,裤子是同样宽松的直筒裤,将她原本纤细的身形衬得有些空荡。长长的黑发没有像往常那样扎起,而是柔顺地披在肩头,发尾带着自然的微卷。她手里捧着一个白色的陶瓷杯,杯口袅袅升起带着奶香的热气。
她似乎正望着窗外逐渐暗淡下去的天色和远处城市的点点灯火发呆,侧影在昏黄的暮光里,显得异常单薄,甚至有些……脆弱?
听到我拉开门的声音,她极其缓慢地、仿佛电影里的慢镜头般,回过头来。
光线从她侧后方打来,将她半边脸颊笼罩在阴影里,另外半边则沐浴在残阳最后的金色中。她的脸色比平日更显苍白,没什么血色,眼下有着淡淡的、青黑色的阴影,像是没有睡好。但她的神情,却平静得可怕。
不是强装的镇定。是一种从内而外透出来的、近乎死水般的平静。那双总是清澈或带着疏离的浅色眼睛,此刻像两口结冰的深潭,表面平滑如镜,映不出任何情绪的波澜。
我就那样,手里捏着那张罪证般的试纸,一步步朝她走过去。
脚下是柔软而厚实的羊毛地毯,吸收了所有的脚步声。房间里静得可怕,只有我自己的心跳,在胸腔里擂鼓般轰鸣,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、城市傍晚的车流声,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。
直到我在她面前站定,近得能闻到她杯中牛奶淡淡的甜腥味,能看清她丝绸家居服领口下,那截纤细脖颈上微微凸起的、脆弱的血管。
然后,我将手里那张已经半干、皱得不成样子、却依然宣告着某个惊天事实的验孕试纸,缓缓地、摊开在她眼前。
惨白的卫生间灯光早已被抛在身后,此刻卧室里昏暗的光线,让试纸上的红色线条显得有些黯淡,但那两道杠的轮廓,依旧清晰得如同用刀刻上去的一般。
苏晴的目光,极其缓慢地、从窗外挪回,落在了那张试纸上。
她的视线在上面停留了几秒。时间仿佛被拉长了。她长长的、浓密的睫毛垂下来,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,完完全全地遮住了她眼底所有可能泄露的情绪。
没有惊慌。没有失措。没有被人撞破秘密的狼狈。
什么都没有。
她只是极其缓慢地、仿佛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耗费巨大心力般,将手里那杯还冒着微弱热气的牛奶,放到了旁边矮几光滑的玻璃桌面上。
陶瓷杯底与玻璃桌面接触,发出一声清脆而孤单的“叮”的一声轻响。在过分寂静的房间里,这声响亮得有些刺耳。
做完这个动作,她似乎才重新凝聚起一点力气,抬起眼,看向我。
她的眼神依旧很静。像深秋季节,山林深处无人打扰的湖泊,水面平滑如镜,倒映着头顶寂寥的天空,也清晰地倒映出我此刻站在她面前、因为紧张和无数翻腾念头而显得有些僵硬、甚至有些……狰狞?的面容。
她没有直接回答我无声的质问。
反而,微微侧过了头。
目光似乎越过了我的肩膀,落在了我身后,落在了我浴袍松散遮掩下、依旧平坦安静的腰腹位置。她的视线在那里停留了片刻,眼神里没有任何探究或评估,更像是一种……确认?一种了然的、带着无尽疲惫的印证?
然后,她重新将目光转回,与我对视。
嘴角,极其轻微地、几乎难以察觉地,向上弯了一下。
那弧度浅淡得几乎算不上是一个笑容。没有温度,没有暖意。更像是一种历经沧桑后、对命运荒诞安排感到无力、最终只能化为一声叹息的、疲惫至极的自嘲。
“我怀孕了。”
她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很轻,很平,没有任何起伏,听不出喜悦,也听不出恐惧或悲伤,像是在陈述“今天下雨了”这样再平常不过的事实。
但紧接着,她吐出的下一句话,却像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,狠狠砸进了我因为震惊和无数猜测而翻腾不休的心湖:
“但我打算打掉。”
打掉?!
我猛地愣住了,瞳孔骤然收缩。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而冰冷的手狠狠攥紧、拧了一下,传来一阵尖锐的钝痛!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四肢,指尖却更加冰凉。
打掉?为什么?!
那可是……至少一千万啊!是田书记亲口承诺的、沉甸甸的、足以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巨额财富!是摆脱目前这种仰人鼻息、出卖身体生活的一条可能路径(哪怕这路径同样肮脏)!是她苏晴,这个如今同样被困在这里、看似平静却难掩疲惫的女人,可能获得的、为数不多的、实实在在的“补偿”!
她怎么会……想要打掉?
难道……田书记私底下给我的那个承诺,她并没有得到?还是说,她知道了我也怀孕的事?她是在……让我?或者,是在用这种方式,表达某种无声的抗议?抑或是……
无数个混乱的、带着刺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疯狂冲撞,几乎要将我本就紧绷的神经扯断。我看着苏晴平静得过分的脸,试图从上面找到一丝一毫的破绽,一丝算计,一丝不甘,或者哪怕是一丝绝望。
但我看到的,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、认命般的疲惫平静。
似乎看穿了我眼底瞬间掠过的震惊、猜疑、以及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一丝不易觉察的……松了口气般的侥幸(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感到一阵齿冷),苏晴又轻轻地、用那种平淡得近乎残忍的语气,补充了一句。
这句话,像一根淬了冰又浸了毒的细针,精准地、毫无阻碍地,刺破了横亘在我们之间那层早已脆弱不堪、布满裂痕、勉强维持着“姐妹”或“共犯”假象的薄膜,直抵最鲜血淋漓的、名为“过往”的真相:
“毕竟我们曾是夫妻。”
曾、是、夫、妻。
四个字,轻飘飘地从她苍白的唇间吐出,落在傍晚昏沉安静的空气里。没有重量,却带着千钧的力道,沉沉地压在了我的胸口,压得我呼吸猛地一窒,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曾经……夫妻……
那些被我刻意尘封、锁进记忆最深处、几乎要假装不曾存在过的画面,那些属于“林涛”和苏晴的、平淡琐碎却真实温暖的日常,像被打翻的颜料罐,瞬间不受控制地、汹涌地倒灌出来——
狭小却温馨的旧公寓,厨房里飘出的家常菜香;两个粉雕玉琢的小家伙在地毯上爬行嬉闹,咯咯的笑声;深夜加班回来,客厅留着一盏小灯,和沙发上蜷缩着睡着的、等待的身影;一家四口挤在并不宽敞的旧沙发上看电视,孩子吵着要爸爸举高高……那些我以为早已遗忘的、属于“丈夫”和“父亲”的责任、温情,甚至偶尔的疲惫与不耐烦,此刻都如此清晰、如此鲜活地闪过脑海。
而这些温暖的、带着旧日尘埃气息的画面,与此刻身处的、奢华冰冷却弥漫着情欲与金钱气息的房间,与站在我面前、平静地说着“打掉孩子”的苏晴,与我这个穿着浴袍、肚子里怀着另一个权势男人骨肉、心心念念着一千万的“林晚”……
割裂。
荒诞。
令人心慌意乱的割裂与荒诞感,如同冰冷的潮水,瞬间淹没了我。
苏晴顿了顿。
她的目光,再一次,落回了我的小腹位置。这一次,停留的时间更长了一些。眼神里,极其复杂地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——像是一夜未眠后深深的疲惫,像是对久远过往某段时光的短暂怀念,又像是一种深不见底的、对命运与自身处境的、无声的悲哀。
然后,她继续用那种平淡的、仿佛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的语气,说了下去:
“我已经为你生了两个孩子了。”
为、你。生、了。两、个、孩、子。
这几个字,不再是轻飘飘的。它们像一把生了锈的、并不锋利却沉重无比的钝刀子,一下,又一下,缓慢而扎实地,割在我刚刚被回忆和现实割裂得鲜血淋漓的心脏上。
是的。
林晚。林晨。
我们的一双儿女。
我曾经(作为林涛)亲眼见证,不,是曾经参与(尽管可能参与得不够)的,两个小生命的孕育与降临。
苏晴十月怀胎的辛苦,日渐沉重的身躯,孕吐,浮肿的脚踝,夜不能寐的辗转;分娩时撕心裂肺的疼痛,产房里压抑的呻吟和汗湿的头发;新生儿响亮的啼哭,手忙脚乱的第一次哺乳,无数个被婴儿啼哭打断睡眠的深夜,泡不完的奶粉,换不完的尿布,孩子生病时焦灼的不眠不休……
那些我曾经觉得理所当然、甚至偶尔会因为工作和压力而嫌烦、想要逃离的琐碎日常,那些被她(苏晴)独自或主要承担起来的、漫长而艰辛的岁月……
此刻,从她口中如此平静地、甚至带着一丝疲惫厌倦地说出来,却带着血淋淋的、无法回避的真实感。
那些苦,那些累,那些被生活磨掉的青春与光彩,是“林涛”亏欠“苏晴”的。是身为“丈夫”,却未尽全责的亏欠。是“男人”对“女人”的亏欠。
而现在呢?
“林晚”站在这儿。顶着年轻美丽的女人的皮囊,肚子里怀着另一个男人的、带着明确价码的孩子,心心念念着那一千万。甚至,在听到苏晴说“打掉”时,内心深处,竟可耻地、悄悄地松了口气——因为潜在的竞争者(在田书记那里,或许也在那笔钱上)可能消失了。
一种强烈的、几乎要将我整个人都吞噬掉的羞耻感和荒谬感,如同岩浆般从心底喷涌上来,灼烧着我的五脏六腑。我的脸颊滚烫,耳朵嗡嗡作响。我张了张嘴,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,干涩发紧,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连一个音节都挤不出来。
苏晴似乎并不需要我的回应,也不期待我的忏悔或辩解。
她微微移开了视线,重新望向窗外。暮色已经彻底吞没了最后一丝天光,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,星星点点,遥远而冷漠。她的声音变得更轻了些,几乎要融化在逐渐浓重的夜色里,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、认命般的疲惫:
“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”
我的钱,就是你的钱。
这句话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。
她是什么意思?是在说,即使她打掉这个孩子,拿不到田书记承诺的那笔钱,她认为我(林晚)将来从田书记那里可能得到的一切,也会有她(苏晴)的一份?因为我们“曾经”是夫妻?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孩子,血脉相连,利益也与共?
还是说……
这是一种更深层的、带着绝望意味的捆绑与宣告?
在这个由王明宇构筑、由田书记加码的、华丽而肮脏的泥潭里,我们早已是同谋,是共犯,是拴在同一根耻辱柱上的祭品。我(林晚)的罪孽,有她(苏晴)的血泪作为见证;她的不堪,有我扭曲的过往作为映照。我的钱,必然沾着她的屈辱和付出;她的存在,本身就是我背叛与堕落的活证据。
我们早已无法分割。
无论是以“林涛和苏晴”的方式。
还是以“晚晚和晴晴”的方式。
“生孩子带孩子太累了。”苏晴最后说道,轻轻地、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。那叹息里没有抱怨,只有一种真实的、深入骨髓的、对重复这种耗尽心血过程的深深倦怠,“我想,”她的目光最后一次,极其快速地扫过我的小腹,“你也最多只能生两个吧。”
说完这句话,她重新端起了矮几上那杯已经彻底凉透的牛奶,凑到唇边,小口地、安静地啜饮起来。眼帘低垂,不再看我。仿佛刚才那场足以掀起惊涛骇浪的对话,只是一段关于天气或晚餐的、平淡无奇的闲聊,已经结束,无需再议。
我站在原地。
手里早已空无一物。那张皱巴巴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
发送任意内容至邮箱po18de@gmail.com获取最新访问地址